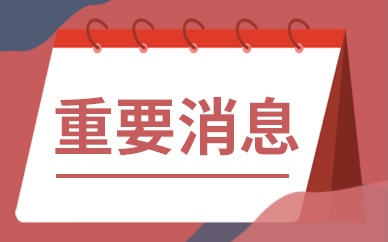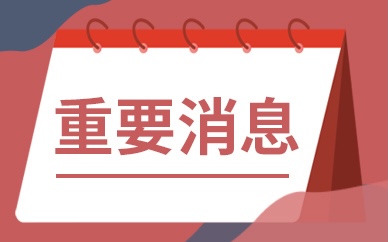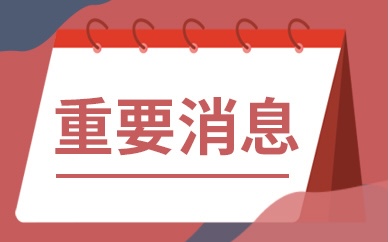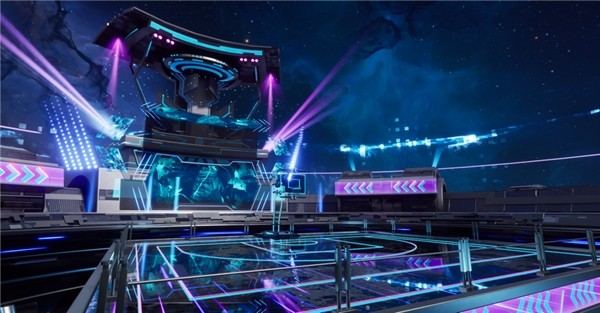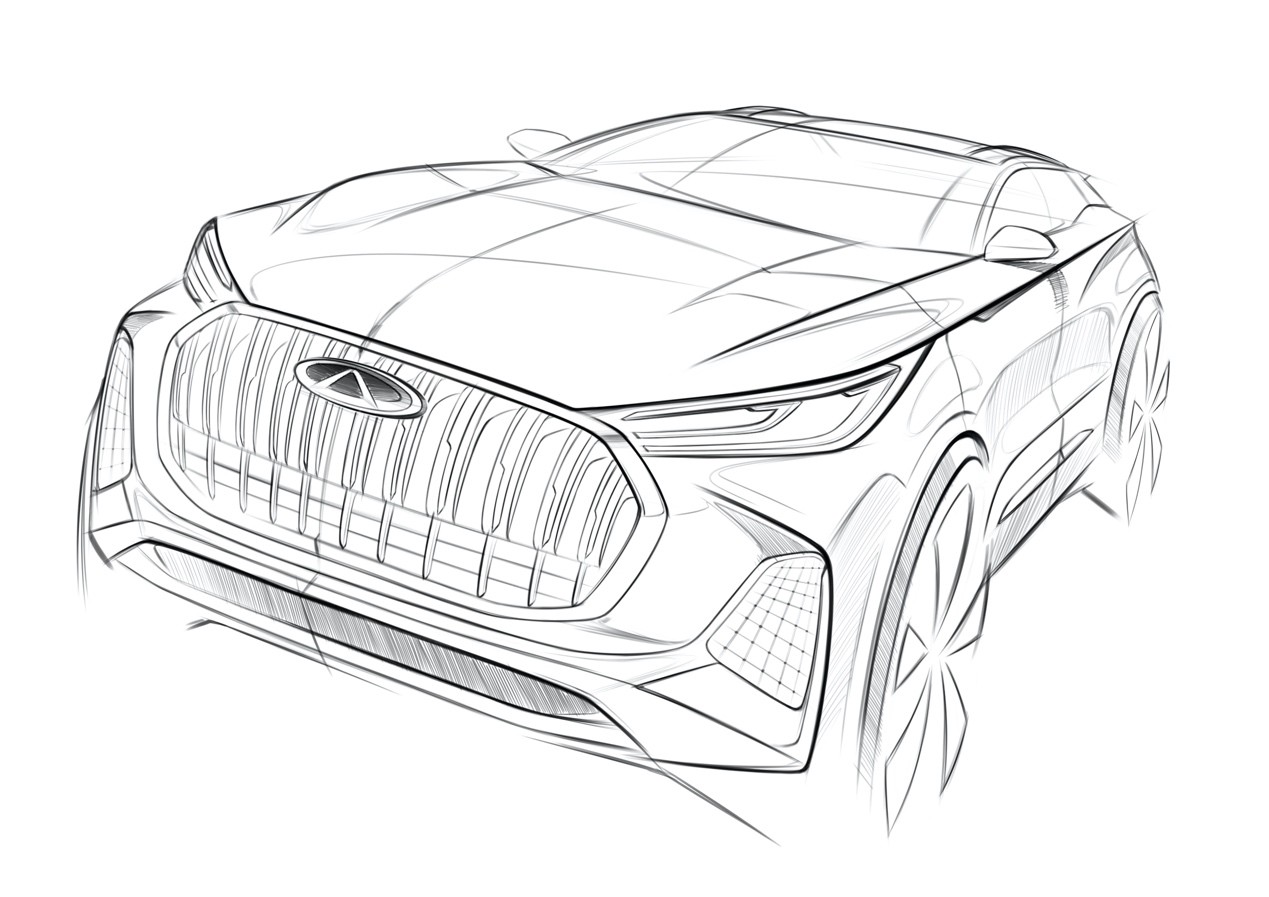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3年元旦的夜晚,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小县城早早结束节日庆典,被黢黑的山脉吞没。
 【资料图】
【资料图】
凌晨3点,一个人影出现在小区昏暗的路灯下,他中等个头,体型偏瘦,身着深蓝色羽绒服。他哈出冷气,直打哆嗦,灌了铅似的腿又不得不迈步前行。
不是罪犯,也非赌博酗酒者,这位75岁的老人,被睡眠抛弃了。
为了能入睡,老陈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一般,一步接一步,直到走够两万步。他揣着最原始的渴望:或许身体的疲惫,可以唤来困意。
老陈不是个例。从生理上,随着年龄增加,人的睡眠易紊乱,继而在紊乱中减少,严重者会干扰生活。有调查指出,中国老年人群中41.2%患有睡眠障碍。
但老年人全群体的睡眠障碍,就像老陈的深夜——隐秘,寂静,不为人知。
老陈难眠,最终住院老陈从磁性材料厂退休了20多年,去年最“多灾多难”。
生活中的变故一件接一件,把睡眠一点又一点地夺走,直到最终因失眠而住院。
9月底,老陈骑摩托与汽车相撞,头上缝了12针,一根肋骨折断。人活了下来,但心爱的摩托车被交警没收,他不能像往常那样自由出行了。
紧接着又迎来新冠的感染高峰,他和妻子即使深居简出,也没逃过感染。12月底,老陈的微信不断传来坏消息,兄弟姐妹、子孙后辈、相熟友人都陆续感染。元旦后,连妻子也病倒在他面前。
只会做疙瘩汤,平日过度依赖妻子照料的老陈情绪逐渐失控。病榻上虚弱的妻子让老陈害怕,“她平日身体硬朗,会过不去这道坎吗,到时候我怎么活?我这么老了,能挺过去吗?”
死亡的臆想裹挟住老陈,加重了他原本偶发的睡眠障碍。自妻子病倒开始,老陈开始整夜整夜地难以入眠。
睡眠不足感觉像地心引力在加重,一股多余的力量将他向下拖拽。他的脸变得更加松垮,颈部赘肉形成的层层褶皱,几乎将他的脸拉成一个长方形。
失眠之后,老陈感到手臂、腰、大腿愈发沉重,每多做一个动作,负担便加重一分。他很快变得气喘吁吁,随之烦躁不已。
夜里,任何声音,不论是来自手机、电视里咿咿呀呀的声音,还是老伴的絮语,都让他莫名地愤怒。后脑勺每次触碰枕头的瞬间,都是一阵天旋地转。只有站立、行走能暂时缓解不适。
家里暖气燥热,睡不着的深夜里,出门,到天寒地冻中走路,成了老陈过去几个月寻找睡眠的“处方”——走两万步,直至眩晕散去、腰酸腿疼、身体困乏到极限时,才能获得两三个小时的睡眠。
当凌晨出门成为常态后,老陈发现,小区里竟然会遇到同样睡不着、在黑暗中徘徊的老人。他们像是游荡在另一个时空的灵魂,彼此擦身而过,都被“睡不着”所折磨。
疲倦不堪的老陈勉强入睡,又被琐碎的噩梦缠绕。有时,他梦到周围到处是死去的人,或是自己做起老本行,一刻不停地修水管。还会梦到和已故十年的朋友争吵,醒来之后大发脾气,“连死人都欺负我”。
“人迈入中老年,出现睡眠问题非常普遍。”北方某三甲医院慢性病管理科主任燕虹向八点健闻表示,随着雌性和雄性激素褪去的影响,加上因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和产生的心理冲击,失眠会越来越频发。
“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波等人在论文中提到,中国老年人群中41.2%患有睡眠障碍,43.6%合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慢性病,44.2%~60.2%患有慢性疼痛,9.8%~22.5%有明显抑郁症状。
但到了临床上,主诉睡眠障碍的老人却很少。“大约只有10%~20%,但实际被失眠困扰的老龄患者,实际会超过半数。” 燕虹说。
据燕虹观察,门诊上,大多数老年人不愿意说“我睡不着”。老年人失眠经常合并焦虑、抑郁情绪,但多数患者对焦虑、抑郁有病耻感,常常以头痛、乏力、心前区不适、胃肠道症状、疼痛等躯体症状为主诉。
而少数主诉失眠的老年患者,又有一部分会因为对吃安眠类药物有恐惧心理,担心形成依赖,拒绝通过吃药去改善睡眠。
燕虹很无奈。她担忧这部分老年人硬扛着失眠,直到病情愈来愈重,才到医院就诊。“失眠急性期如果及早地控制,未来可以完全脱离安眠类药物。但一旦拖成慢性,不仅睡不好,也离不了药了。”
在夜里漫步,就没能挽救老陈的睡眠。
连续多日睡眠严重缺乏、叠加新冠感染后,老陈终于住进了医院。他无力起床走路,身体忽冷忽热,眉头紧锁,呻吟不止。安眠药加到四颗,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住院期间,护士给老陈注射了安定针,被剥夺已久的睡眠终于重新降临。精神科医生给老陈开了新的安眠药,让他过段时间再去复诊。出院后,妻子的病情也有所好转,老陈悬着的心才落地。
最近,老陈每天依旧小心翼翼地“养着”睡眠,排满日程——出门散步跳舞,打两小时麻将,听舒缓音乐,服用安眠药,夜夜期待凌晨时分的睡眠能如期而至。
消失的睡眠,难获得的安眠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幼年、青年和中年,睁眼的时间几乎都在各种光源下度过,而衰老则延长了凝视黑暗的时间。
对大多数老年人而言,时钟在凌晨的走动并不陌生。
一点钟的夜晚什么样、两点钟什么样;三四点钟起夜时,屋里家具的神态、旧照上模糊的人像什么样;黎明前的黑暗里,哪些鸟开始叫早,清洁工在哪条街上清扫;或是雨疏风骤,楼上同样失眠的邻居下床走动了……睡不着的老人通通知晓。
正月初三那晚,78岁的乔芝睡不着。
失眠的凌晨无所事事,乔芝掰手指头数数,想算算过完年自己几岁,从1945年数起,55年、65年……一直到2015年。黑暗中,她看不清掰了几根手指头,反反复复数了好多遍,才算清楚自己今年78岁。“还好,算了算,自己还没糊涂。”
她的安眠药在床头柜里,平时睡不着就摸黑吃一片,努力继续睡。
这样的尝试有时也会是徒劳。黑暗中,时间一分一秒流淌着,乔芝的思维变得异常活跃,各种琐碎的小事浮现在脑海。想来想去,又要起夜,一看时间已是5点多。看眼窗外,天快亮了,她想再睡一觉,闭上眼睛,糊里糊涂半梦半醒,再一睁眼,时间走到了7点半。
这样的昼与夜是乔芝近几年的常态,但她习以为常,在乐观的她眼里:自己至少有药,有时候也能睡得挺好。
“我的朋友没有安定类的药,她说她的药不管用,就把我女儿给我开的药拿走了,说终于睡了个好觉。”乔芝说。
在当地医院主诉失眠,医生只能开出阿普唑仑、地西泮等安定类,也就是苯二氮䓬类药物。这类药物属于列管的精麻类药品,一个人的医保账户一次只能开7片,这远远不够日常使用。
去年,乔芝的女儿索性收集起好几个人的医保账号,一次性去医院开整瓶(100片/瓶)的阿普唑仑。
过去的几年里,她陆陆续续这样开了4、5次药,最多的一次开了4瓶,一共400片阿普唑仑。但由于安定类药物不易得,需求量又大,在当地医院很紧俏,药房的人也想要,“到现在,医院药房还欠了200片没有给我。”乔芝的女儿说。
开出来的200片阿普唑仑,乔芝分给了妹妹100片。几年前,妹妹的爱人突发车祸去世,她由此患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几乎每夜都睡不着。
后来还有熟人来问乔芝要安眠药,她都推辞说没有。开药不容易,自己和家人都需要安眠药,舍不得给别人,“只能保证我和家人的使用。”
但在医生看来,这样的做法也隐藏着风险,失眠的老人需要到医院挂号。
沈阳安宁医院精神康复中心主任王会秋接诊了一些自行用药的患者。一些老年人对精神科有顾虑,不愿意来找医生看病,反而爱看朋友发的抖音,互相推荐吃什么安眠药。很多人到王会秋门诊来,“上来就说就给我开这个药,我跟他一样。”
“我说你现在知道一样的部分了,但你还有不一样的部分。”王会秋只得跟这些老年人挨个科普一遍失眠症诊疗方法和安眠药用药注意事项。门诊的老年患者里,大约有30%需要用安眠药。王会秋觉得,老人互相推荐安眠药,可能还会造成滥用。
但即使如此,如前文所述,在现实生活中,去医院治疗失眠的老人太少了。
另一个极端:被滥用的安眠药失眠的老年人,一边极度渴望睡眠,一边却远离医生、忽视疾病。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容易把老年人的睡眠求助推到两个极端——有老人过分担心副作用,睡不着也不用药,就那么熬着;而另一些则把安眠药当作“灵丹妙药”,极易服用过量,甚至成瘾。
根据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陈奇等人的研究,长期连续应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容易产生药物滥用。在改善焦虑及睡眠等临床应用中,用药时间原则上不应超过4周,老年患者更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及时停药。
但现实中,大量服用安定类(苯二氮䓬类)等精神类药物等老年人没有遵循医嘱。
一项针对吉林省社区3376名老年人的研究表明,超过85%的老年人家里常备精神类药物和止痛药,明显高于其他药物。超过70%的老年人存在凭个人感觉服用、经常服用精神类药物,以及不遵医嘱和自行停药的现象。
南京梅山医院医学心理科医师袁心崧,经常与过量服用安眠药的老人“斗智斗勇”。
她几乎每次门诊都能碰到一两位这样的老人,开药的理由都很类似——之前的安眠药找不到了。她担心这些老人的耐药性越来越强,服用安眠药量不断增加,从一天吃几片到十几片,“最后类似于吸毒吸死。”
袁心崧说,“有一些老人的抑郁、焦虑,光靠现有的精神药物是没有明显改善的,就可能会有物质滥用的方式代替。”
每种安眠药可以开出的最大剂量不同,如右佐匹克隆的最大剂量是35片,思诺思、劳拉西泮是28片。有的老人像爱芝女儿一样,拿全家的证件一次性开出大量安眠药;也有的人叫外卖、同城跑腿,让外卖员用自己的身份证开药。
袁心崧为此还举报过平台,甚至举报到公安系统,至少遏制住了她身边的这些现象。
她称自己是“开安眠药的守门人”,能辨识出异常用药的患者。医院的处方系统也增加了超量开药、频繁开药的警告。公安也会监测安眠药使用,会找开安眠药量较多的医生了解情况。
她有时也感到无奈,有的老人“滥用”安眠药是为了自救。他们病痛缠身或是焦虑抑郁,出现睡眠障碍,当过量服用安眠药之后,病痛神奇地消失了。“他们用自我麻醉的方式来缓解病痛。”
有一名70多岁的老抑郁症患者,偶尔出现在袁心崧的门诊。患者本身抑郁、焦虑的症状很明显,治疗多年之后,他发现只有通过吃药才能缓解他抑郁、焦虑。最夸张的一段时间,每周都会有这名患者家里的不同人,带上全家的身份证来医院开安眠药。估算下来,他一天能吃掉20片安眠药。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老年精神科主任郑克注意到,很多老年人用上安眠药后便减不下来。
他的门诊患者里,大约有30%需要服用安眠药,很少有老年人用上安眠药后能收放自如地减下来。原因在于安眠药很快能起效,而且苯二氮䓬类药物还可以抗焦虑,老年人服用后很快可以进入舒适区。“对老年人来说,他不用面对他的冲突。原来好像很慌张、睡不着、很烦躁,现在一次睡着了,这就是灵丹妙药。他就离不开了。”郑克说。
临床治疗中还有更现实的问题。
在睡眠门诊时,康宁医院睡眠中心主任郑天生,一天要接诊将近60个患者,平均接诊一个老病人大约用时5~10分钟,新病人大约20分钟。治疗睡眠问题,医生不仅要问病情变化,还要看上次用的药有没有效果和副作用,以及病人最近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有无经历压力性事件等,以便相应地增减药物。
因为问诊时间有限,一旦病人不断换医生,又没有主动提出要减药,医生忙起来没有时间从头到尾问一遍,“医生就给你开药了。”
安眠药随意增减都会适得其反,减药太快后,加倍地用药,也会造成药物滥用。
沈阳安宁医院精神康复中心主任王会秋所在的医院,由于地处市郊,患者来一趟不容易,王会秋尽量给每个病人10多分钟的问诊时间。王会秋感到,较长的问诊时间起到的效果非常大,可以跟病人交代清楚。
“老人存在不存在焦虑?实事求是讲,他就是焦虑。用药没有错,用药方案也没有错。只不过说,就像你给学生生活费似的,他生活费不去吃饭,反而买游戏币了。”王会秋说。
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郭兮恒主张老年人有睡眠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请睡眠专家来评估。“安眠药本身是处方药,合理用药对于病人来说很棘手,但对于医生来说是每天都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