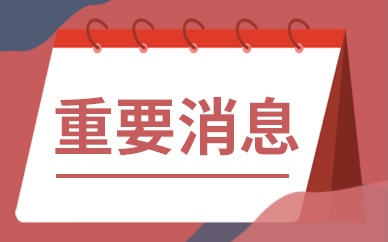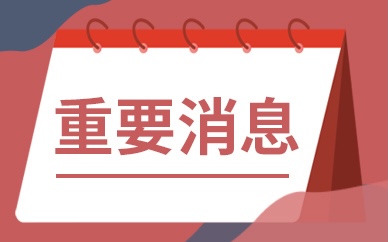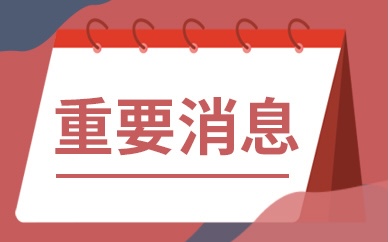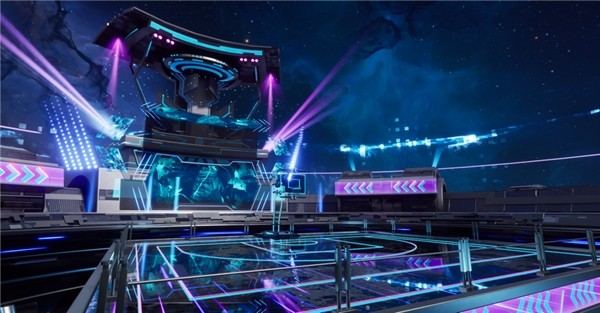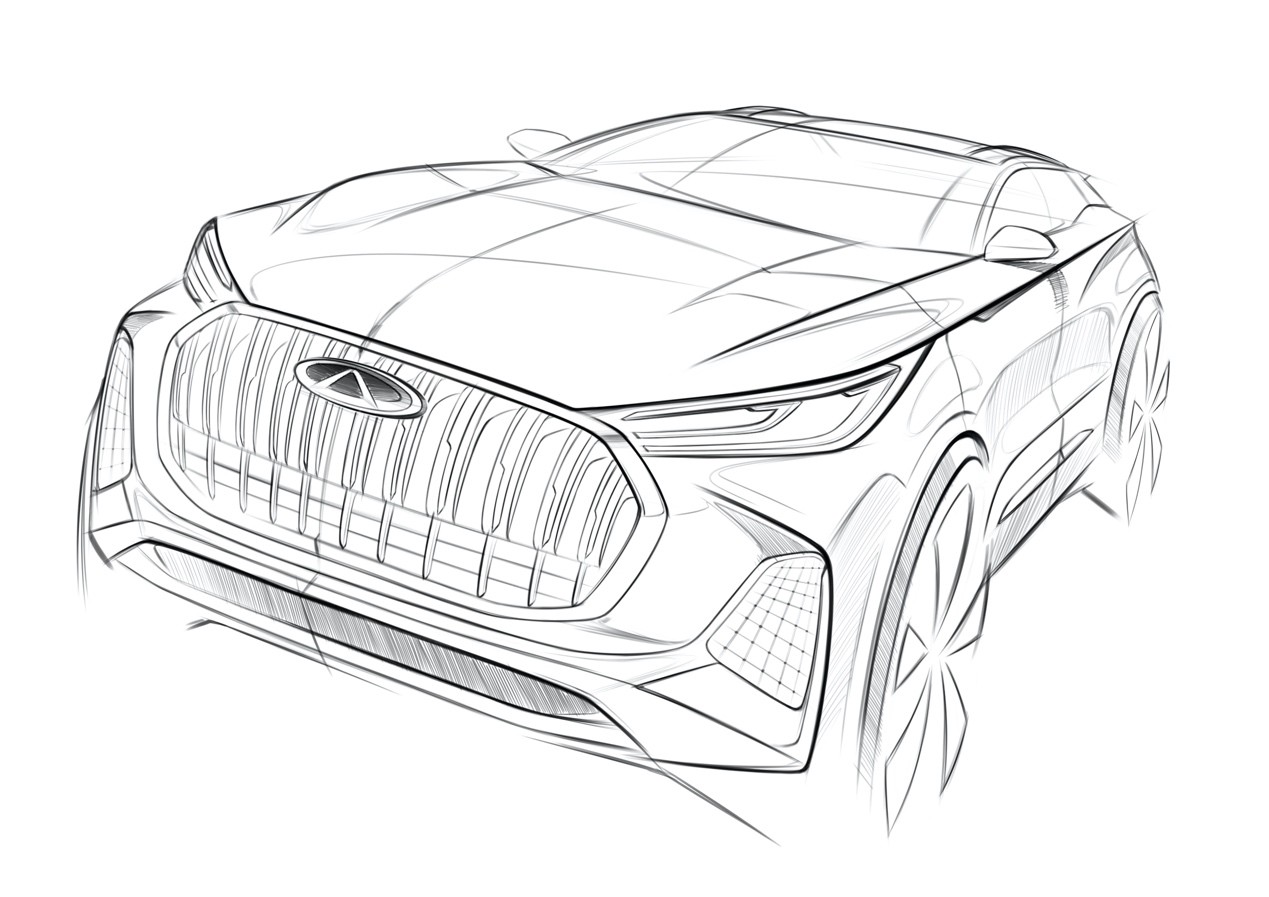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3年2月,恒瑞子公司luzsana日本地区临床研发总经理Kiyoshi hashigami 发文告别Luzsana。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还记得去年5月,恒瑞野心勃勃地推出全球化子公司Luzsana,被视作出海大动作。luzsana的高管也都很有来头,美国、欧洲、澳洲、日本地区都有外籍高管坐镇。然而短短三个月后,开始陆续有外籍中高层从Luzsana离职,包括恒瑞美国/欧洲首席执行官Scott Filosi,恒瑞美国/欧洲首席医学官Joseph E. Eid。离职的外籍员工最短的入职不过5个月,Luzsana成为他们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最短暂的一段经历。
不只是恒瑞,另外一家被称为“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创新药企,即使海外临床团队还未裁员,但也面临“海外高管又贵,项目推进又慢”的难题。
外籍高管离职的可能的原因有很多,Luzsana是由中国传统药企创办,海外基因缺乏,恒瑞方与子公司外籍员工之间的沟通磨合是个问题。外籍员工的收入高于本土,前期的投入产出比不会太漂亮。
此外,中国的医生很多时候会在医院/协会/科技项目/地方政府等因素的要求下,参与到某个重大创新药项目临床开发中去,而中国的药去美国等海外地区做临床,没有这层“关系”,他们就是纯粹的看数据,以及药企投入多少。
无论如何,高管团队持续失血,都存在临床交接的成本,意味着临床进展将拖慢。对于和时间赛跑的创新药企,这将是雪上加霜。
去年中报电话会上,恒瑞曾表示吡咯替尼海外临床暂停,恒瑞给出的原因是来自第一三共8201的竞争压力太大,但深究下去,或许也和海外临床费用太高有关。一位知情人士也表示,Luzsana海外临床研发没有完全停止,但暂停了一些项目。其中,恒瑞最受关注的医药“双艾”方案在去年5月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达主要终点,但快一年了,直到如今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临床不顺利与团队离职的因果关系不明,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海外PI对me too类药物不感兴趣。PI是临床中非常重要的角色,相比亚洲,欧美地区PI在各领域的影响力更大。
当初国内药企野心勃勃的自主出海,如今一路磕磕碰碰。老大哥恒瑞尚且如此,之后再有药企想自主出海,很可能望而却步。借力出海也没有那么容易,在所有创新药出海的故事里,药企都要用时间和金钱“交学费”。
残酷的现实仿佛在逼问创新药企,还要不要出海?如何出海?
当出海成为必选项70亿的市场一定比14亿的市场大,这是所有行业的人时候都会去讲的一句话。
医药行业这两年聊出海聊得格外多,一方面是支付端改革带来药企“躺着赚钱”的情况逐渐消失,加上未盈利企业上市的窗口收缩,资本望而却步,这也给市场规模带来了压缩。因此,变相倒逼资本对双创项目做出更挑剔的投票;另一方面,当下药品的质量背书的的确确仍然是以美国FDA为权威,中国的药品要拉到其他五大洲卖,得到美国FDA的认同,这是必经之路。
所以,其实在“国际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还没那么高时、在“全球化的Biotech”这个概念还没被大部分提的时候,国内一些看的远的制药公司们都在尝试着做这件事。
比如早在2011年,和黄医药就旗下两款小分子抑制剂(赛沃替尼和呋喹替尼),前后分别和阿斯利康和礼来达成合作,首付款加起来也超过一亿美金,这要知道当时国内药企的营收规模大部分还都不到两位数,还是以人民币计价。
2013年的百济,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它会是“三地上市,融资百亿”神话的主角。它找到了阿斯利康,准备用一款RAF抑制剂和一款Parp去向这家当红MNC大厂换一些现金,来度过当时还比较寒冷的融资环境。但后来接手的却是默克——阿斯利康当时并没有看上这家中国刚起步不久的Biotech,后面找了默沙东合作Parp。
再之后,这种国际化的BD交易就更多了:恒瑞的PD-1授权给Incyte(虽然后面被退回),康方的CTLA-4卖给默沙东,信达跟礼来全面合作大分子肿瘤药......
这些都是国内药厂早期做的一些尝试。而随着各种华人XX协会、校友圈子、区域联盟等社群的普及和壮大,从供给端给中国的生物创新药出海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场景和机会。也是在这之后,每年去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ASCO(美国肿瘤年会)和JPM(摩根大通医疗年会)上露露脸,成了国内稍微有实(yu)力(suan)公司的标配。
2020年后,以加科思、百济和天境为代表的和海外药企的三份大单,把这种授权合作的出海方式推向了高潮,不仅带来景气度上的高升,也算是给国内做创新药的公司打了一个样:什么样的产品,找什么样的公司,谈了什么样的条件,才是标标准准的“国际化”。
这种热潮也使得制药行业里的BD成为比CMO更炙手可热的职位,因为在当下本土市场容量天花板有限、但短期海外销售难以成型之下,license out成为许多药企NO.1的选择。
但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出海远远不是一纸交易这么简单。
新时代,新要求首先是大洋彼岸监管要求的变化。
2018年7月FDA肿瘤学卓越中心(OCE)主任理查德·帕兹杜尔(Richard Pazdur)受邀来到上海张江交流访问,受到一众科学家和生物药创业公司热情欢迎和接待。回国后的老帕第二年在AACR(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上高调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PD-1,哪怕仅仅只有中国本土的临床数据。这位FDA审批改革的风向标的话语直接加速了国内四大PD-1公司的海外申报进度。
但这份热情持续了不到三年,老帕的态度就发生180度大转弯,直言新时期下,“仅靠一个国家的临床数据”和美国要求的患者多样性原则相违背。然后很快就有了信达的ODAC(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会议。后面,东西要拿到FDA注册,全球多中心临床成了标配。
而另一边,MNC(国际大药企)眼光不比监管端标准低多少,也逐渐看重MRCT(全球多中心临床)的数据。
徐诺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英霖曾公开透露,徐诺在和一些海外药企谈授权转让时,对方都希望看到在III期临床里有当地人种的患者数据。一旦揭盲,双方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的谈判。在此之前的所有合作仅停留在数据交换的阶段。
如果以NDA和BLA获得FDA批准作为出海成功标志的话,目前国内出海成功的药企,都有海外基因。
百济神州和传奇生物的主营主体在美国,上市地点也在美国,一定程度上类同于一个美国的公司。
去年获FDA批准上市的本维莫德,是由国内企业天济医药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First-in-Class。但继续追溯历史,天济医药创始人陈庚辉最初在海外就开始研究本维莫德,归国后将研究成果带回,继续研制。
他们一开始走的就是国际化路线,体现在团队上。
纯本土药企出海或许雇得起外籍高管,但不一定用得动,因为未必能做到(加班)文化上的契合。依赖外包可能更糟糕,90%的CEO都对CRO有所不满。结果反倒是很多CRO和药企回过头培养本土的人才,再将他们输送到海外研发中心。
预算(钱)的问题也绕不开。
在美国,基本在一位临床肿瘤患者身上,需要花费16万美元左右。徐诺药业一度低估了预算,认为美国和欧洲是中国的1.5倍,后来到了操作层面发现费用是不够的可能是本土的2-4倍。
这背后有两层原因。一个最最直观的是中美人均GDP的差距,美元计价下,海外临床无论是涉及到的物料还是人工成本都要比国内高一个层级。另外,美国的生物医药行业,相比全球医药平均水平又是一个更高的倍数,美国医疗GDP占比高达17%,这是其创新药&医疗服务高定价的本质。
本身物价水平高,叠加上医药行业高上加高,二阶乘数之下,整个大健康行业里的任何一个需要花钱的环节,都要高出国内一个数量级。
资本的寒冬下,企业需要精打细算,思考哪个地方效率高、资源充分,哪个地区反映这个药物的特点。比如从一家药企的角度,创始人认为与其花10万美元一个人在澳大利亚做临床,还不如扎扎实实花16万美元在美国做好数据,减少FDA的质疑。
追根溯源,又回到了临床需求的问题上。
在未被满足的疾病领域,FDA鼓励疗效确切且突出的药物通过加速通道上市,但也希望尽快提供验证性临床结果。这个时候即使用中国患者数据,FDA也会用欢迎的态度。
在已有供给的疾病领域,FDA更希望看到后续新药的验证性临床结果,尤其偏好于MRCT(国际多中心临床)、 头对头(对照同类药物或标准治疗方案)、优效性设计。
临床数据是最终的评价标准,而它又是现在这个阶段去向资本市场要钱的唯一筹码。
因此,回到企业要不要出海这个问题上,或许最终还得要研究和开发部门来回答。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