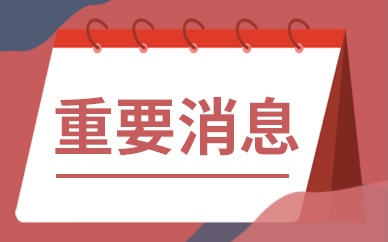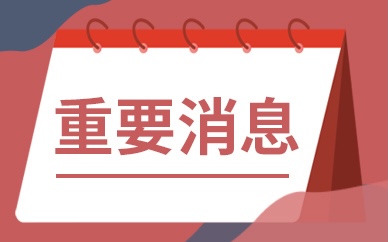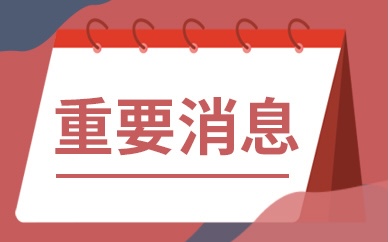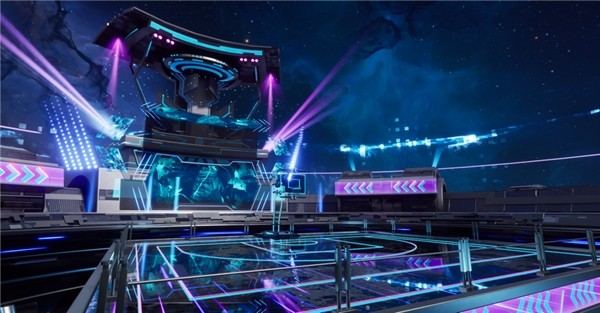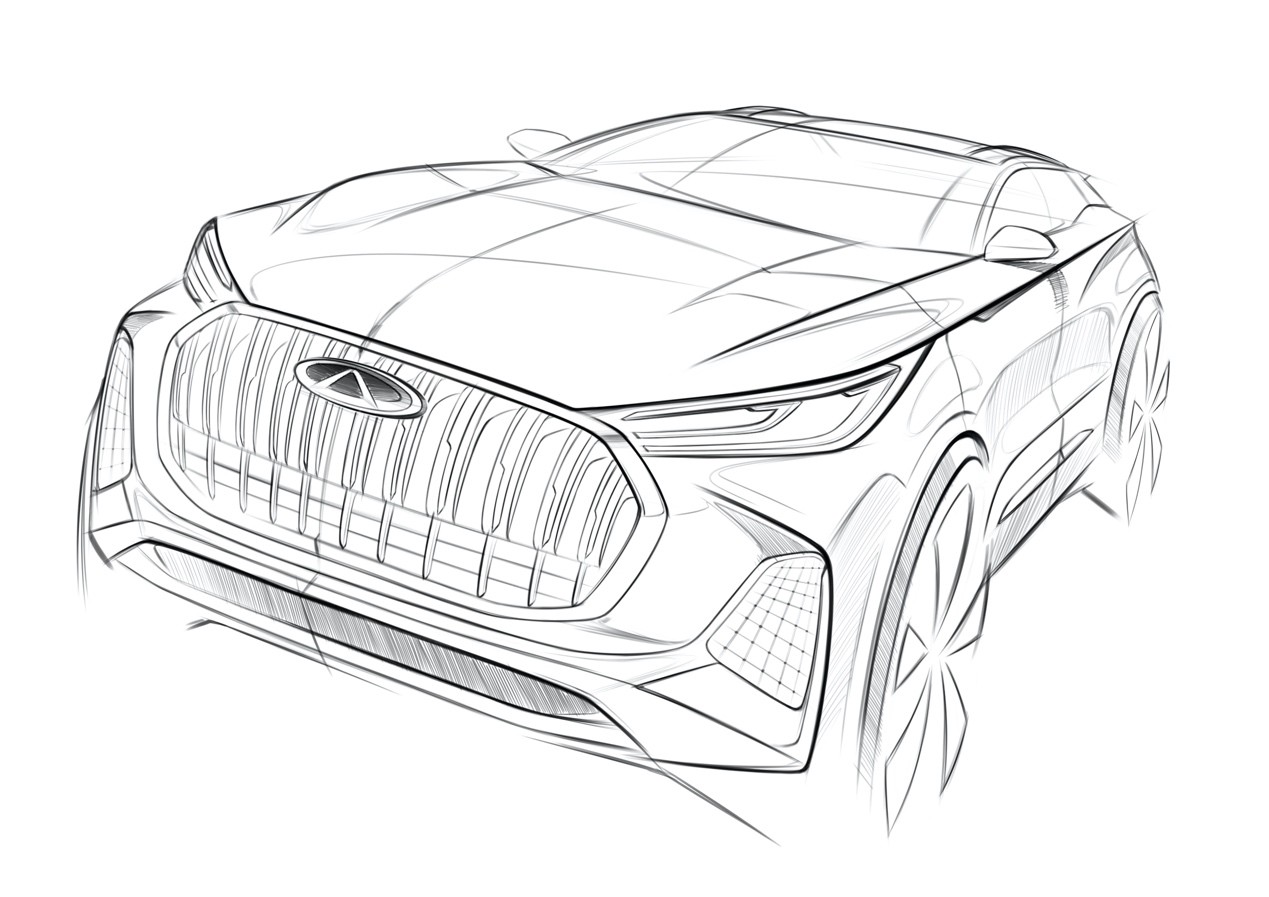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2022年,创新药市场的气候几乎在一夜之间从春意盎然到秋雨萧瑟。
这年春天,一家刚成立的明星创新药企信心满满地融资。创始人本想“好好挑一挑”,不料却门庭冷落。
而在此前一年,这家药企的创始人稍作透露要创业的打算时,登门拜访的投资人就已如过江之鲫。2015年以后一级市场兴起了创新药投资热,但在PD-1医保谈判压价后,国内的支付天花板已经非常清晰,而且,这个天花板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低多了。出于对投资回报的忧虑,一级市场也开始谨慎起来。
虽然创新药投资市场上马、立项、掏钱然后等着滚雪球的淘金神话已经破灭,但搭上这路顺风车的创新药企却无法就地撤离,它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让企业运营下去。出海,这个曾经言之尚早的路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Biotech的新方向。
“出海”有三种途径,股权并购、license out和海外新药研发。这几条路径并不冲突,药企可以根据不同阶段的自我定位做出不同选择。其中,海外新药研发被公认为是最难走的路,也是走通后最稳固的路、真正全球化的路。
很多年来,中国有原料药、中间体、仿制药,但无创新药。如今想要出海的Biotech的创始人乃至研发人员,大多本就是从美国“回流”而来。他们多在年轻时出国留学或者工作,在美国扎实的制药工业中成长、成熟并身居高位。当他们看到国内创新药兴起后,放下稳定的工作回国创业另辟天地。
中国广阔的市场曾经极具吸引力。但他们当初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后风云突变,自己又主动或被动带着在中国研发的药“杀”回美国。
过去几十年,中国药企与海外的经贸关系也从属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大体定位中。美国药企搞创新,中国药企做生产,再销售往全球。中国的原料药企业曾经借力旧有的全球化供应链,一飞冲天。
而到了Biotech出海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国药企在海外做临床,是打破原有的全球化固定模式,将中国药企在全球供应链的定位中往前移。
要做全新的事是很难的。前段时间恒瑞传出砍掉海外临床团队,这是一个新的坏消息。在海外进行临床、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国药企尤其是新生代的Biotech们并不熟悉,尤其是患者招募、药政法规方面。这成为了众多Biotech出海过程中的难题。
目前,除了百济神州外,尚无国内的Biotech在美国成功上市新药。也有一些Biotech已经在海外临床耕耘,劲方、和铂、亚盛……这些上市或者还未上市的药企都已经默默走在出海路上好几年,它们遇到的难题是中国Biotech们共同的难题,它们的积累也是中国Biotech们共同的积累。
原始积累期,传统药企的粗放出海中国药企的出海是“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最早开始抢滩出海的药企是一批原料药企,华海、海正、东阳光药……它们的首发出海方式也并非交易授权或海外临床,而是原料药和仿制药。
由仿制药开始,是因为美国的ANDA(仿制药申请)和NDA是完全不同的流程。
“仿制”是指其与该上市药品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规格、服用方式及适应症等。ANDA不需要提供临床前(动物)和临床(人体)数据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基本上,在通过FDA和欧盟的GMP后,只需要提供产品生物等效性的证明材料,仿制药便可以生产并上市。
好些龙头原料药企业都走上了这条路。1977年,海正以八万元买断中科院研发的克念菌素,成为国内最开始吃到甜头的原料药企业。1992年,海正获得了第一个FDA证书,此后,海正有多类原料药和制剂通过FDA批准。华海也是类似旅程,而东阳光药则走了另一条路。
2006年,东阳光药获得罗氏关于奥司他韦在中国的专利授权许可,东阳光药目前为国内最大的奥司他韦生产商。东阳光也是国内药企中较早通过美国、欧盟的GMP认证的,它生产的一批原料药和制剂都通过了欧盟官方和美国FDA批准,而其布局的奥司他韦,在罗氏的专利到期后在国内的销售大放异彩,一个药养活了一家企业。
这批传统企业的枝条向海外延伸,广义上,为中国的药物出海奠定了基础。而到了创新药这里,情况就变得不一样起来。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要做的不再是原料输送、外包生产,而是做知识产权创新,成为全球化医药供应链中更主动的一个链节。
大部分Biotech的海外临床首站都选在美国。原因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这里是全球创新药最大的市场,也是全球创新药最活跃的地方。美国的FDA是全球审评监管药品最权威的机构,拿到FDA的NDA(新药上市申请),相当于拿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药政部门的“敲门砖”。
同时,FDA也“艺高人大胆”,优先鼓励创新。“拿肿瘤产品来讲,美国是相对鼓励创新药的。如果FDA认可早期临床数据,有可能在临床数据还不太完整的时候,它也加速后续的审批流程。”一位Biotech的临床负责人表示。
而且如果后续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欧盟递交NDA,由于在美国提交的临床数据可以滚动提交给欧盟,欧盟得到的数据更加充分相对完整 ,往往可能会在美国优先审评的适应症基础上扩大适应症,一举两得。这些条件都适合Biotech的需求和特点。
同时,美国的药价也是全球最高的,不仅远高于中国,也远高于欧洲。有人以全球销售额前25的药品为基准来对比,大部分国家的药价比美国低了接近8成。保护专利的制度、高度自由的市场、多重支付体系,使得美国的药价常年维持在全球最高水准。
不过,美国药价高的主要是创新药,仿制药比中国还便宜。“沃尔玛零售200多种专利过期药,基本普药都有,一个月的药量价格只4到15 美元。”一家美国Biotech的负责人吴野(化名)表示,常见仿制药价格如此之低,是一种市场调节的鼓励创新模式,国内的集采是另一种形式的将仿制药价格回归合理范围。
总体而言,美国是一个利润高、而且能稳定高下去的市场,而且它的准入证就是“创新”或者“同类最佳”,一旦获准进入,这家Biotech的实力会立即得到背书。上市后,新药哪怕不在美国卖,在美国的首发定价也能左右其他国家市场的定价。由此,许多出身美国大药企的Biotech老板们评估,这是一个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搏一搏的目标。
但前提是需要有能力。
转型创新期:Biotech的海外临床痛点去年信达和和黄的遇挫,使得国内Biotech的出海之路难度更加拔高了一层,似乎除了百济神州这种有能力高举高打、三地上市的创新药企外,其他的Biotech要在创新药申请上抢滩美国,似乎可类比蜀道之难。
抢滩动作早的创新药企就有了优势。
2017年,某Biotech创始人正面临临床地点的选择。“相比全球同类项目,我们管线的头部项目进度并不落后。”这名创始人当时评估后认为,而国内一些拥挤的靶向药赛道必然饱和,比如多一个或少一个PD-1也无所谓,越内卷,在后端就会难做。
“要做到全球新就要最先做出全球临床验证。”这名创始人认为,把风险前置好过风险后置,在技术上花的成本,未来商业回报上总会赚回来。于是,他们选择了在海外做临床。
这家刚刚成立的Biotech,选择了先在澳洲做临床。
创始人最初是希望“拿一些海外的临床数,未来也好做海外交易”。澳洲的药政部门审批更快,适合开展某些产品的I期健康人群试验。
在中国和美国,药企的临床试验申请要先递交到药监局和FDA,由这两个部门从整个方案的独立材料、相关文献、临床前数据、临床设计角度对药企的临床做出审查。而与中美不同,在澳洲,伦理委员会在一开始起的作用最大。
“在澳洲要做临床,是先递交到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只要伦理审核通过后过了,企业就可以去药监部门TGA备案,之后就可以开始临床。”一家在澳洲开展临床试验的Biotech创始人回忆。澳洲的临床申请时间快,非常适合和时间赛跑的Biotech。
但是,这批先出发的创新药企也遇到了另一个这几年专属的危机:新冠疫情。
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在做一期临床时,健康志愿者相对国外更好招募。而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一家创新药企发现海外的健康志愿者招募颇为困难。虽然他们早有预测,但没想到的是,在疫情好转后,健康人群依然入组很慢,“最后多方问了下,原来之前入组的很多人是背包客,疫情好转后他们回去工作了,就不来当志愿者了。”
海外临床试验过程是个不断遇到问题、又需要不断解决的过程。入组慢、数据回收慢、医院停诊,新冠疫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所有药企的临床进度,还有一些另外的挑战,属于只要入局者都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比如产品定位、针对不同国家国情适应症的选择、先申报FDA还是欧盟、对照组的设计、受试人群的甄选招募等。
一些微小的差别里,都暗含乾坤。比如,鼻咽癌的患者多为亚裔,慢粒白血病的患者中国人则较少,中美罕见病的图谱更是差异很大。对药企来说,这其中可能就暗藏着“坑”。
2021年,康弘药业宣布停止康柏西普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在 68个试验中心中,有一半以上的受试者视力在注射后较基线变化等于甚至低于零。在公告中,康弘表示这与试验药物既往的临床研究以及真实世界大量的使用经验有很大差异。海外临床花费甚巨,任何药企都不会拿没有把握的数据去赌博。这个国际三期临床失败,或许就是不小心跌入以上的几个坑内。
一个药企的海外临床前数据再好也不代表它就能获得三期临床成功,但另外一些明显的管线和临床设计缺陷则必然招致失败。有的药企一开始瞄准的是国内“人傻钱多”,管线比较安全和老旧,现在如果想用这些管线出海,当然不太容易。
比如申报一些所在国家并不缺乏的药品,这意味着最起码也要临床做到非劣结果,这也并不容易。“如果是一些常见的Me too,国外的市场竞争已经很大,如果再去重复想获批临床就比较困难。”
入乡随俗也并不容易。虽然Biotech们的创始人和高管团队多有海外基因,但药企不同管线细分程度和门槛都很高,很多Biotech刚出去组建团队时并不熟悉当地药品审批政策。
运营一个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需要面对不同国家不同药监部门的不同需求,光来回的拉锯沟通、反复修订就需要花很长时间,而Biotech还必须组合好不同国家药监部门的反应时间,整体进行项目规划,以免因为衔接不好而误事。
各国审批的流程、周期,以及监管部门关注的问题都各有特点。“美国的反馈还算快的,基本在一个月内。而在欧盟申报相对复杂,除了要考虑临床方案在哪个国家更容易实施,不同国家的审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冒出来。”上述Biotech临床负责人解释。
从创新药企需要“小钱办大事”的角度,海外临床还必须考虑风险点的控制,“比如风控点的制定,在临床前加哪些实验,在一期临床制定哪些指标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是国内一些药企在海外开临床项目的潜规则,万事以面子过得去为先。但对资金和时间都有限的Biotech来说,此路不通。对它们来说,当遇到临床不顺利的问题时,在恰当的时间止损,也好过不停砸钱进去把失败圆回来,“哪一个指标不过关,就可以马上停下来,把损失减到最少。”
除了海外临床的执行本身,中国创新药企出海临床和海外授权还会遇到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Biotech的高管多是科学家,对于法律的条款、流程和细节了解得并不精准,干预的时机不恰当。
“比如谈授权时,条款清单签订了、尽调做了,在最后签最终协议的时候,突然说要改首付款金额。”一位做海外并购的律师表示,中国一些Biotech的交易法律思路还局限在中国境内企业之间交易模式上,这是他做的案例中Biotech们遇到最大的问题。不过,据其观察,目前这个问题上,行业共识也已经有了普遍提升。
硬币另一面:海外临床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的Biotech艰苦卓绝地在海外“突围”时,也有海外的Biotech想进来。在中美两地Biotech出海的比较视野中,也能看到中国Biotech在海外做临床也有一些在地优势。
吴野是美国一家Biotech的负责人,他所在的公司有一个罕见病管线即将开始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国是其中一个临床中心。据目前国家药监局对进口药的审评政策,该药在美国获批后,药企也可以拿着中国患者的这部分临床数据申报在中国上市。
来中国上市罕见病新药的美国某Biotech,目的并不是为了销售,对于它来说,这是顺手之举。
新药需要申报国际多中心临床,中国是在亚洲的最好选择,“以日本为例,在日本做临床有一些很独特的要求,包括在入组国籍种族方面。”这家美国Biotech的负责人吴野(化名)表示,日本的临床要求复杂,跟PM沟通难度大,流程冗长,一些小分子口服药的临床试验也需要住院患者。
国外的创新药企来中国申办新药,一方面由于中国能找到入组患者,且医药临床环境相比过去好了很多;另一方面也是有先在中国市场上“插旗”的意思:“药是全球性标准统一的,除了外包装的印刷可能有差异,其他生产步骤都要求一模一样。所以你这个药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卖,相当于药的价值没有体现。”虽然目前罕见病的主要市场不在中国,但吴野认为,中国的市场瞬息万变,罕见病市场也渐有风起之势。
基于熟悉中美两国药政的比较视野,吴野认为虽然国内的Biotech在美国的临床道路充满挑战,但也有很多积极的面向。中美两国临床申报的时间差不了太多,另一方面,中国的药监部门也有另一方面的“挑剔”,中国的生产方面要求更精细严格,而且报临床要分别报遗传办和伦理办,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很长。
此外,在中国做临床研究承接方必须是医院,而美国很多诊所也能做临床研究。相对而言,中国有1000多个GCP可以开展临床,而美国的GCP数量多出不少。因此,中国的Biotech在美国上临床,不需要排队等少数的大医院大专家,吴野指出,“美国医生专家沟通容易,成本也低。”
至于海外临床研究具体执行方面,目前国际CRO市场非常成熟,药企的不少临床研究也外包了出去,临床设计都可以借助CRO的力量。在吴野看来,Biotech最不可避免要去克服的问题,是对申报当地药政的不熟悉,“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也是出海的药企必须掌握的东西。”
国内的创新药想出去,国外的创新药要进来。这种现象的背后,是2015年毕井泉担任国家药监局长改革后,中国创新药和审评环境在极短环境内和国外接轨,是一种正向的流动。
如今,中国的Biotech出海之路,目前正处于一个节点上。中国的创新药试图走出去,更加体现了过去7年里中国Biotech们集体实力的增强。
几位Biotech的创始人,都曾提起在美国申报临床时,总会有一两个美国临床PM(项目经济)颇为苛刻。几位创始人认为,这并非是美国整体思潮或者环境的影响,而是由于中国Biotech此前并没有集体的成功范例,一旦有几家创新药企开个好头,先申报成功一两个药,后续的药企申报上市就容易一些。而一旦现在开始往海外临床出海的方向努力,这一天就不会太远。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