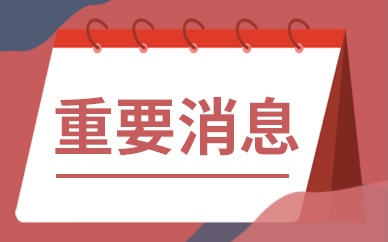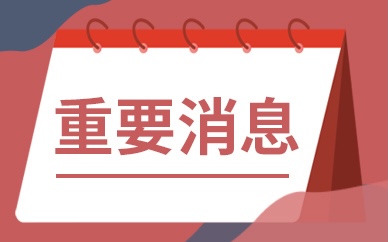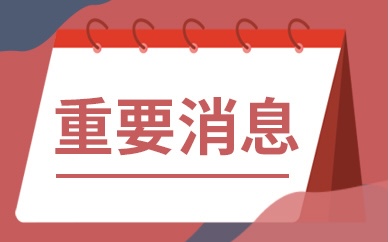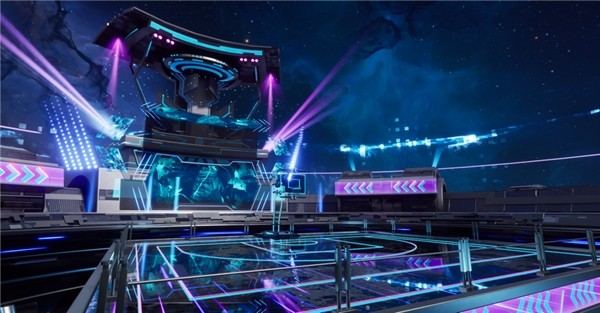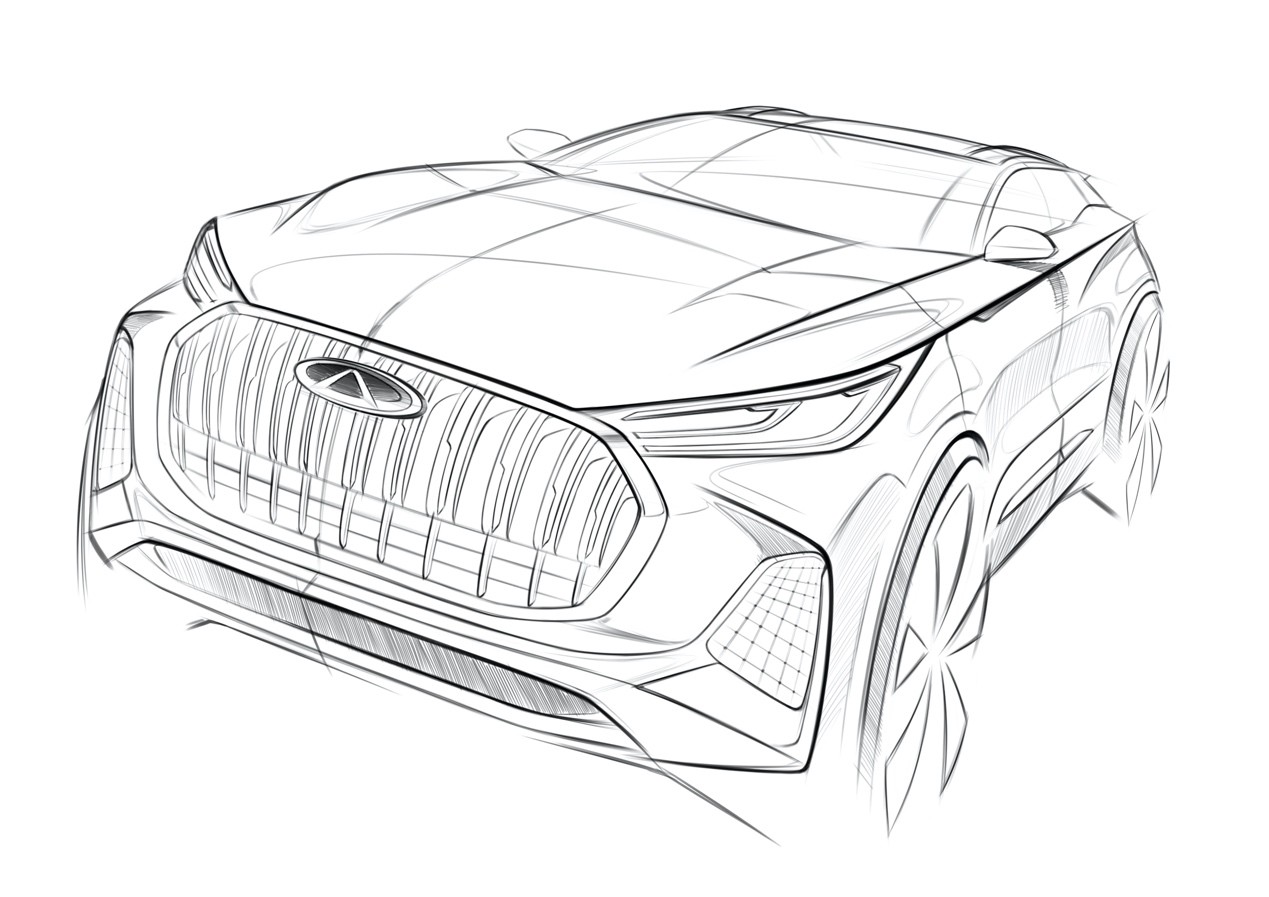自西方亚里士多德奠定了以“看”为中心的认知方式,“观”及其关联的“视觉”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自我以及他者的主要路径。
在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即对于“听”的重视,并自觉将“视听”予以并举。这一传统从先秦出发,蕴藏与展现在后世众多的文学名篇与诗词歌赋中。
成就听觉的审美之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听”制衡着人们急于言说而不善于聆听的莽撞,平衡着视觉给人们带来的功利与急躁,让我们变得更加谦卑、包容,进而走向自我、他者乃至世间万物的深处和远方。
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开张圣听”,提醒统治者广开言路的重要,凸显“听”在政治决策中吸纳意见的功能以及保障决策正确的效用。
李煜《相见欢》中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塑造了一个无言寂静的无声之境。此时的李煜在想什么?他听到了怎样的心声,是懊丧、悲凄,抑或悔恨?
两相对比:一个是开耳迎接外界的意见,一个是闭耳迎接内在的心声;一个是言语的丰盛,一个是言说的缄默。一开一闭、一喧一静呼应对照,展现的是“听”的来去收放及其之于国家、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寂寞无言,还是喧嚣吵闹,都与听觉引发的情感有关。登上岳阳楼的人,既因为“满目萧然”的视觉引发落寞,也因为“虎啸猿啼”的听觉引发悲伤。视觉与听觉在此交融为一,与个体之情密切关联。
田园诗歌中的“听”,同样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在声中悠然自得迎来新的一天。诗人在充满喜悦、活力的鸟鸣中睁开眼,以声音迎接事物的到来,以事物体味声音的美妙。
在这一互动中,还有以“听之声”而想“事之果”:“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到夜晚的风雨声,不知花又落了多少。在欢喜与活力中似乎又掺杂着一丝哀伤,让“听”与“事”“情”产生连锁的关联、互动的生成。
这不禁让人想到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同样是听到昨夜“雨疏风骤”,卷帘人得到的结论是“海棠依旧”,李清照以“绿肥红瘦”予以质疑。这是听者由“听”而形成的不同之“象”,也是由“听”对接生成的不同之事。
说到田园中的“声”给予人的闲适与快然,怎能忘了陶渊明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狗吠声、鸡鸣声这些属于农家的特有之声,既展现从容不迫的生活状态,又给人以丰富生动的画面,成就了听觉的审美之功。
喧闹之下自有静处。
先看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空山之中虽无法由视觉而见人,却可以由听觉而闻人。视觉所存在的局限,听觉来弥补。由听而闻人语,由听确证人之存在,由听迎来他者。听将个体与外在世界(自然界与人之世界)连接起来。
再来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人在闲适时,既是静看花开花落之象,也是静听花开花落之声,聆听自我之心声。在鸟儿的声音响彻山涧时,人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产生了联系,将人从自我之世界拉回现实,形成个体内心与外在时空的交织。“声”与“听”勾连了人与自然,连接了内外。
修身齐家治国融为一体
“听”不仅能迎来心声,也能迎来家国的兴旺、铁马的驰骋。或欢喜或悲伤,皆源自士大夫之于天下的关切与情怀,源于个体与国家命运的休戚相关。
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一听闻便泪流满面,是欢喜之情的漫溢,是由“听”将自我的情绪与国家的起伏紧密结合,让修身、齐家与治国融为一体。
对杜甫来说,有喜悦之时,亦有悲痛之时:“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鸟之鸣何以惊心?是因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看到国破家亡,那让王维感受空寂山谷中幽静的鸟鸣,也成了惊心之音,摄人魂魄。这些起起伏伏的情绪,因听而来,由听生情,家国情怀在“听”中动人心扉。
在“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中,“听”将风雨声转化为金戈铁马的奔腾与呼啸。在这个梦发生的时候,战场之声与风雨之声融为一体,也许都化作了陆游纵横的老泪,展现了诗人的豪情与壮志。梦与现实已分不清,这也许是“听”给予陆游最好的慰藉。
同样是夜雨,同样是聆听,苏轼显得轻松了不少:“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没了外在的慷慨激昂,夜雨都化入内心的坦荡达观。这份经历起伏而来之不易的心境,让人读来有点心疼,也有些感佩。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雨和风在“听”中被赋予生命,活泼泼地到来。它们已不是风雨本身,而是苏轼人生的起落写照,“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样的人生坦荡于苏轼不是一蹴而就的,于任何人亦复如是。所以,不同年龄听着同样的内容,所听到的以及所折射出来的心境会有很大不同。
比如,“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同样是“听”,同样是“听雨”,“情随事迁”也是“情随时迁”。人生的跌宕与情绪的起伏在“听”中展现、迎来,给予人以生命的回响,成就生命的厚度。
“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真谛,也可以帮助我们探寻事情的真相。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探寻“石钟山”命名真相时,便是通过“听”完成的。他与苏迈泛舟于山下,听到各种声响,最后在水声、冲击声中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这里被命名为石钟山。
这是沿着声音给予的信息和脉络去追寻真相,不人云亦云,尽力还原人与事真实的样子。这种精神在“听”的践行中展现、在“听”的探寻中成就,让人对“听”这一认知方式刮目相看。
“听”可以是“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自得其乐,也可以是“檐头溜,窗外声,直响到天明。滴得人心碎,聒得人梦怎成?夜雨好无情,不道我愁人怕听”的愁苦万端,还可以由“声”之听而成乡音、乡情:“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听与情感密不可分,故乡的模样在声中形成,对故乡的思念便在听中生成。听与情的背后都是人。碰撞出的是人生的坦荡,还是梦中的激昂,抑或无奈的悲叹,都取决于人对听的践行与想象。
这种源自先秦而成的“听”的传统,在文学的表达中变得柔美而温婉,并由此蒙上诗情画意而呈现出某种美学意蕴,彰显着人世间的千姿百态与生生不息。正所谓:“烟火村声远,林菁野气香。乐哉今岁事,天末稻云黄。”
(作者:伍龙,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